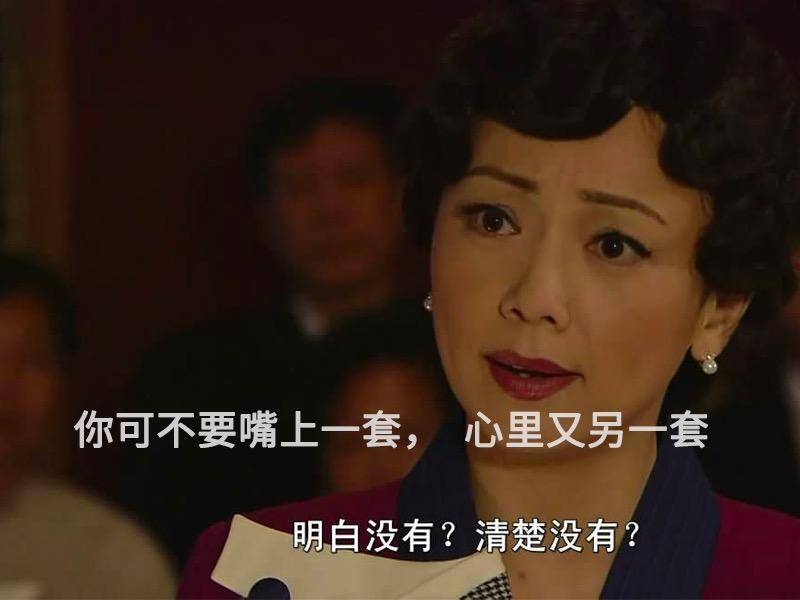
公开信( Republic of letters )是单读的新栏目。这是一个开放的项目,来自不同背景、住在不同国家的作者,在这里向彼此写信,分享他们最近的生活、关心的议题、以及世界上重要的事。今天这封信是原新京报记者柏琳写给朋友吴琦的信件。文学究竟可以做什么?是很多喜爱文学,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面对“文学何为”的问题,柏琳放弃做一个观察者,而是重新学法语、练搏击,回归到普通人的日常。她在信末反复提到的“强壮的悲观”,也许是应对“丧”的解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dandureading),写信人: 柏琳,原《新京报·书评周刊》资深记者、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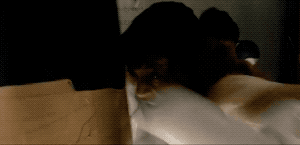
打个招呼,对自己笑一下,两个住所相隔不到六公里的朋友,写信给彼此,并期待收到回复。在一个用微信秒传表情的世界里,这似乎颇具喜感,希望接下去的倾诉不会太破坏喜感。
现在是四月的尾巴,也是我辞职半年的节点。毕业以后,在类似于乌托邦的地方做一份热爱的书评工作,学习了 7 年的语言学理论,我放弃得义无反顾,只想和有温度的书为伍,像赫拉巴尔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塑造的废纸回收站打包工汉嘉那样,把珍贵的图书从废纸堆里捡出来,把它们递给心灵渴望得到抚摸和重塑的人们。我做文学,我渴望用文学来爱。

近五年,做了很多小说诗歌和剧本。全情投入时,萌生一种幻觉,以为靠自己微弱的力量能为读者带去一点点美的愉悦,或者思想的痛点。制作一个个专题,哪里的作品闪过一道亮晶晶的光,就努力奔到哪里去。这种幻觉持续了很久,文学是否可以重塑心灵?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作为一个副刊的记者和编辑,是否能够胜任好这摆渡人的角色,把作品让渡给读者?当我们越来越觉出宏大叙事的虚妄,那么从细微处切入的个体叙事是否真的可以从细微处修补我们的疲倦?
金宇澄在谈自己的非虚构作品《回望》时,说到一个观点,成为我的痛处,那感觉就好像被打了一记闷拳。面对现实,无论你如何穷尽修辞术和文字天赋,事实最真的部分也都烂在了肚子里,那么,文学是无力的吗?我懵了。
我猜想,我的力不从心,就是从那个自我质疑的时刻开始的,幻觉的泡泡马上要破了。
后来,我们知道了台湾女作家林奕含被性侵的事件,她只留给世界一个问题:文学是道德溃败的帮凶吗?
又后来,北京“清理外来人口”,有一群被赋予了“鼠族”称号的人几乎一夜之间被赶到一个叫“北京站”的地方,从网友拍摄的照片里,我们看见孩子无辜的眼睛,年轻母亲无泪可流的麻木的脸,她们需要的是哪怕是一平方米的庇护,而文学艺术能做什么?拍下照片,写下观点激烈的自媒体文章,在朋友圈刷屏,被 404 以后寻求其他渠道继续接力?
再后来,大学教授性侵女生的丑闻频频爆出,我们一边愤怒,一边习惯了愤怒,乃至成为一种标配情绪,个体能做什么呢?如果文字既可以证清白,又可以掩是非。现在,并不遥远的叙利亚民不聊生,而我们隔岸观火,沉默无言。
有网友在豆瓣上写下状态:是我们生来就太懦弱?还是这个世界不让我们坚强?又有人这样写道:“丧”恐怕要在未来成为一种常态的社会情绪,80 后艰难地“将要‘被’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而 90 后,根本不想工作,没有恋爱的欲望,也没有生活的欲望。

我如鲠在喉。自己构建起来的幻觉堤坝在塌方,我无法面对一个出租屋被推倒的悲伤的北漂青年说,来,我们读几首穆旦的诗,你能振作一点。我无法对着一个遭遇性侵的女孩说,逃到文学里去吧。我丝毫不认为被推倒的出租房和贫民区的废墟可以成为任何艺术作品的对象,我痛恨一切悲情的展示和苦难的贩卖,可我恰恰不知道文学能做什么。难道听凭几个诗人在小圈子里转发几首阿拉伯诗歌,或者召开一个“我们这一代为什么这么失败?”的作品研讨会,文学就可以做什么了吗?
文学不能直接参与社会行动,却有个悖论摆在我眼前:面对废墟,是拿着纸笔从旁记录,还是放下纸笔,抬起担架往前走,寻找生还者?
我几乎完全否定自己,我辞了职,想寻找更真实的生活。我猜想,从前的生活已经让自己和生活本身隔绝得太远,我害怕成为隔壁大爷大妈眼里的“书呆子”,这不是说我害怕接受别人的定义和评判,而是说我害怕一旦自我塑造成某种封闭的形体,是不是意味着就此停滞,意味着丧失可能,丧失力量,丧失元气。不,我不要自我重复,也不要偏安一隅躲在文学里幻想外面的真实,无论何种境遇,都不要停止创造。
我重新拾起法语课,练搏击,学开车,做饭,修浴室,换灯泡,洗床单,去菜场买菜,给一个老阿姨定期照看菜摊,给父母换保险……写下这些流水清单时,我一点底气也没有,因为知道这不过是普通人的日常,我做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相反,我却因为自己曾长久地忽视而该感到汗颜。

深夜最痛苦,靠阅读熬过它。我十分喜爱尼采,在我看来,他想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既然人生充满了痛苦,既然已经看清了生存的真实状态,我们该怎样做才能让它变得可以忍受?尼采有一个说法,叫“强者的悲观”。尼采认为,强健的生命渴求痛苦,从生命本体的高度,和不可知的悲剧命运力量的抗争,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很像存在主义对不对?不过我想说的不是这些。“强者的悲观”,就是用强健的本体迎接注定走向虚无的宿命。“文学何为”这个纠缠我不放的问题,本身没有答案,去写,去读,去生活,去传递。
不过我很想斗胆篡改一下尼采的概念,我渴望一种“强壮的悲观”,相比“强者的悲观”来说,可能这个概念更契合我周围一片“丧”的氛围。丧啊,不想上班,不想恋爱,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不想出门,不想和人说话,连世界也不想看。无力啊,说句真话也反复掂量,诅咒体制又没有勇气离开,痛恨人情又点头哈腰,鄙视圈子又汲汲钻营,因为拒绝真实,而撕裂了真实。“丧”成了万金油,成为一种可以表演和贩卖的情感,“丧”成了廉价品,不再是抵御成功学和鸡汤的解毒剂,“丧”入侵了内心,我们归罪于时代,环境,体制,出身,甚至运气,惟独那个自己,是可以原谅的。可事实上,哪个时代不糟糕呢?可哪个时代都有星辰,“丧”却悄悄给我们的脸化上了犬儒的妆容。
“强壮的悲观”,它是不是“丧”的某种解药?我不知道。我不会妄想自己可以开解药,尤其当我自己也是一个病人。强者是星辰,我们是地上行走的普通人,生老病死,走向虚无。可姿态实在非常重要,锻炼身体,收拢精神,能不能不苟延残喘,在一片无意义的废墟中立定站稳,强壮地迎接虚无?我猜想某种程度上,古人比我们更懂尊严。但古人不可追,我从市井里寻找。面对废墟,我选择加入寻找生还者的队伍,我不再愿意做拿着一本书在远处观察的人。如果还有时间,救援完成后,我会试一试能不能记录。但首要的,是先迈开脚步,同时不放弃寻找同道人,我眼睛开了雷达。

给你写完信的几天后,我就在贝尔格莱德啦,去多瑙河里捡几块鹅卵石给你,可以做镇纸。那个在火药桶上生活了一个多世纪的地方,据说当地人每天最要紧的事,是抓紧时间多晒太阳多喝几杯咖啡,生命也许转瞬即逝,没有时间丧。
要多笑。
柏琳
剧照来自《百元之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dandureading),写信人: 柏琳,原《新京报·书评周刊》资深记者、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
本文由 单读© 授权 虎嗅网 发表,并经虎嗅网编辑。转载此文章须经作者同意,并请附上出处(虎嗅网)及本页链接。原文链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244008.html